那么,中文里的“鲜”是如何形成的?陈保平用自己亲身经历说明,“有一次我到崇明去,当地人请我们吃一道崇明农家菜,河鲫鱼烧羊肉。这个汤的鲜味是我从没尝到过的。有人告诉我,河鲫鱼烧羊肉汤是中国古代一道名菜,‘鲜’字就是鱼和羊放在一起。这让我茅塞顿开。”
法语翻译家马振骋笑言,“很鲜”干脆直接翻成“veryxian”。就像英文romantic(浪漫),中文就叫罗曼蒂克;意大利pizza就叫比萨,不会说是带着火腿的奶酪面粉大饼。
“鲜”字如何译,真是一个翻译的难题吗?在法语翻译家马振骋家中,82岁的老翻译家聊起这个有趣的话题。
“有些概念确实很难译”,马振骋说,不仅是在食物,更广泛的在哲学中,确有一些概念是中文有、外文无,或中文无、外文有的。“比如鲜,到底是什么感受?你与外国朋友吃饭时告诉他,这种味道就叫做‘鲜’。同样地,比如10年酿、5年酿的法国葡萄酒,一个法国人可以把其中微妙的味觉差别形容得丝丝入扣,而中国人没有这样的体验,也没有相对应的中文词。爱尔兰作家乔伊斯写了一部难懂的《尤利西斯》,后来又写了一部更难懂的《芬尼根的守灵夜》。他深知翻译不易,但相信没有语言是不可以翻译的。我觉得他这话的道理是从最终会达到的目标而言的,什么事说着说着最后总会定下名称,那就是约定俗成。比如‘鲜’直接翻成‘xian’,约定俗成下来,就可能成为外语中的一个新词。”
马振骋说,翻译不是万能的,但翻译是不同文明交流的基础,即便做不到十全十美也不能放弃,这就是翻译。“文学翻译绝不是字与字的对译,句式与句式的照搬。一旦领悟以后,就要努力寻找恰如其分的句子去表述原作的本意与本色。做到形神兼备,原文与译文就如同一对舞伴形影相随,舒展自在。当读者在灯下读你的译作,合上书看封面,记住了你的名字,感谢你带给他好书,这是多么美妙的犒赏。”
转载请注明出处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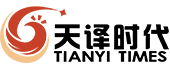
 相关推荐
相关推荐